未来教育的挑战和选择
- 发布时间:2014-02-19 16:13
- 作者:穆耕森
- 浏览量:27296
未来教育的挑战和选择
李 帆
在中国教育史上,过去十年是一座重大的里程碑。短短十年里,大规模的教育投入、各种思潮的激荡与冲击、观念的改变与飞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的面貌。
可是,改革越深入,我们面对的问题就越复杂:新观念的普及,并没有必然带来教育教学方式的革新;寄望于通过课堂的改变来重塑学校文化,目的却远未达到;创新土壤的培养,仍然是举步维艰……
如何才能跨过改革的“深水区”?只用“摸着石头过河”的老思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深水区”,需要我们学会搭梁架桥,用新的、科学的的思路,去找到教育改革新的出路。
缺乏了科学性,教育就不太像教育了
我多次参加教育研讨会,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对比:西方教育工作者发言,或是国内专家介绍国外经验时,他们除了理念,更多谈的是数据、做法和实证。有个事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刚开发出一款游戏软件,帮助小学生学习四则运算。设计者在谈及自己为什么出这些题时,他说,根据脑科学研究,一个孩子完成异母通分时,大脑里要经过四个步骤,他所出的题便是按照这一研究成果而设计的。
与他们相比,中国教育工作者更喜欢表达观念,“以学生为中心”、“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几乎在每个发言人口中反复出现。听得太多了,不免使人昏昏欲睡。即便谈到做法和措施,在回答“为什么这样做”时,也往往是拿出“因为我们要以学生为中心”来解答。
这岂不怪哉?观念指导实践,然后再用这一观念来证明实践。这种“自证”,未免太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了!这也让我们倡导的各种观念,总是高高飘在天上,不容易落地生根。
一年多前,有单位发起“教师对新课改的评价”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新课改的总体评价表示”很满意”的仅为3.3%。“满意”的为21.3%,即只有约1/4的教师表示满意。
原因可能很多,但新课程的可操作性差是原因之一。看看我们的各学科课程标准,薄薄的小册子,变涵盖了三年甚至六年的的学习目标和标准。表述的简单,意味着标准的笼统、简化和不全面。
首都师范大学的邢红军教授曾指出,科学方法至今没有被纳入各学科课程标准,而且各学科课程标准还普遍存在以“科学探究能力”代替学科能力的做法。诸如“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试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等广为流传的“科学探究要素”,其实只是科学探究的步骤罢了,并没有涉及能力的本质。
与我们简单地课程标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标准十分详细,注重课程标准的可测性、严谨性、清晰性和精确性。据统计,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各门主要学科的课程标准累计多达200多个,它们包含的次标准更是多达3093个。像公民和历史学科的次标准分别为427个和407个。
丰富而具体的标准的缺失,是教育缺乏科学性的另一个表现。缺乏了科学性,教育就不太像教育了,教育也无法赢得其他人的专业尊重。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缺乏科学性?
20世纪初,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但是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所惯有的东方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有深刻的辩证思想,却未产生辩证逻辑;有判断,但没有系统论证,更没有由概念和推理组成的文本。简而言之,东方思维中缺少逻辑和实证的精神,而讲究逻辑和实证,正是当代科学思维的主要特征。
缺少了科学思维,近代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没有科学思维,也使我们的教育陷入感性的经验主义的泥淖:在各种观点和口号“贴标签”式的指挥下,有多少人知晓学习究竟是如何在大脑中发生的?有多少人分析过知识的类型?又有多少人研究过不同类型的知识是否需要不同的教学方式……
这些问题回答不好,教育改革的花样再翻新,口号再嘹亮,也不会触及教育的核心,只能是“雨过地皮湿”而已。
说到底,教育改革不仅需要一种形上芬芳的呵护,也需要晶莹剔透的科学理智主义的灯光。
所幸的是,一小部分先行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清华附小,他们研制出了自己的语文、数学、英语《学科质量目标指南》。清华附小的校长窦桂梅说,研制《学科质量目标指南》的目的,就是对国家课程标准进行细化,不仅有知识标准,而且有能力标准,以此“在国家课程标准和教学实践之间,搭建一级级的上升台阶”。
对知识标准和能力标准的补充和细化,并非易事。清华附小在窦桂梅的带领下,整整华了10年时间!
我钦佩于他们用科学思维办教育的勇气,更希望能由国家层面做这件事情。从课程标准的科学性出发,让科学思维慢慢扎根在所有教育者心中,让教育回归“既是艺术,也是一门科学”的本真状态。
“综合改革”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教育改革需要思想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从何而来呢?除了思想的深度和密度外,同时也来自于方法。然而,我们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却没有一个可以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法。很多时候,改革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从而导致十年改革呈现出“局部有效、整体出问题;短期有效、长期出问题”的状态。
用什么样的基本方法来指导改革?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决议在教育部分的第一段里,提到“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其实,“综合改革”不只是一个政策要求,更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这是由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无法预设学生的未来,它只是提供可能性。教育在实质上是不可计算的,全国上亿名中小学生,就有上亿种可能。教育的各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浸透,构成一种独特的生活,一句话、一首歌、一个活动,都可能影响到受教育者的未来。所以,教育改革不可能是一个阶段或一个环节的改革,它需要的是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协同推进。
初步分析,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至少可以分成三分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的,是教育与社会、社区、家庭的协同。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有把社会视作“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的传统。
在国外,常常可见博物馆聚集着学生,他们是到那里上课的;有时候课堂是图书馆,师生席地而坐,读书,交流;有时候,课堂又是社区,教育可以完全融入社区之中。
几年前,苹果企业横空出世。许多中国人羡慕美国出了个乔布斯。但,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乔布斯?
一个小小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从小在硅谷长大的乔布斯,12岁时从黄业上查到惠普创始人休利特的电话。他给休利特打电话,向他要制造频率记录仪的电子元件。早已功成名就的休利特,没有不耐烦地挂掉电话,还让他暑假到惠普实习。
此时,社会、企业、高校甚至个人,都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教育资源的一部分。在这个“伟大的学校”里,可以放飞自己天马行空的梦想。事实上,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学校,给了孩子一个最能促进其生长的宽松条件。
与国外学校相比,如今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比他们好得多。有的国外校长看了中国学校后,连连惊叹:在一些名校里,有几百万元一台的最先进的实验仪器,有几百门的选修课程……但一所学校能给孩子提供多少种可能性?能够穷尽所有孩子的可能性吗?不能。所以,陶行知才会把“不运用社会的力量”的教育称为“无能的教育”。
这种“无能”,还表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社会和家庭,抱怨他们不理解教育,抱怨他们总是向教育传递压力。但我们忽略了教育自身,我们在教育与社会、社区和家庭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大门,从而将教育改革圈定在了一个小小的圈子里,无法突破,无法生长。
改革走到今天,如果我们再不进行宏观层面的综合改革,那么,这次改革所倡导的“适合的、可选择的、多元化的”教育理想,必定受阻。
第二个层次是直观的,是教育各个环节、各个阶段改革的协同推进。如今,大家注重课程、教材、教学、评价和考试改革等五个环节改革的同步推进,尤其把招生考试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中观层次改革改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管办评的分离和政校关系的调整。这是多年呼吁,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学校缺少办学自主权,人、财、物受制于各个行政部门,责、权、利无法统一,学校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庸。曾有局长坦言,自己那里每天都有校长去汇报工作、申请支出,人太多,只好让办公室编号排队。
当学校无法独立办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期待课程、教材、教学等各个环节个性化?如果课程、教材、教学是缺乏个性的,有个性的教育、有创造力的教育又从何而来?
近些年来,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诺丁斯和索尔蒂斯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改革的书。他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自1958年以来的美国教育改革总是不成功?思考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教育改革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每一次改革最后都忽视了校长和教师的主体性,都把他们当成改革的对象,而不是改革可以依靠且必须依靠的力量。
要激发学校和教师的主动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放权,厘清政校之间的关系势在必行。教育改革进行到最后,正如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说的那样:改革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
第三个层次是微观的是学校和教师层面的综合改革。学校层面的改革需要用综合改革的方法和思路,比较容易理解。那教师呢?
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在实践中,很多教师仍然习惯于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专业界限之中,也无法把专业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背景之下。这样的教师,永远无法发挥出教育最大的力量。
因为,一个卓越的教师,必定是综合性的,它本身就是一本多姿多彩的教科书:对世界、对人生有自己的看法,对知识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有坚定的信念,从而使他呈现出一种个性风采。正如学生评价自己的老师、知名文化人顾随时,说他“有时站在讲台上,一语不发,也是无言的诗”。
优秀教师的魅力,正来自于此。
在山东省潍坊北海双语学校,我遇见了一位这样的语文老师,她叫李虹霞。她会用整整一学年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写字教学。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她说:“我不是仅仅让孩子写一手好字,还要让他们爱上我们的汉字,感受汉字的美。”她请求美术老师开书法讲座,上书法课,还和这些一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美学家蒋勋的《汉字书法之美》。
在她的课堂上,语文、数学、美术、音乐被巧妙地整合在一起。像她开设以“月亮”为主题的课,整整两周时间里,孩子们唱的是关于月亮的歌‘用古筝弹奏《春江花月夜》;从《诗经》开始寻找有关月亮的古诗;笔下画的也是月亮……孩子们沉浸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美意象之中,也对这样的课堂产生了深深的眷念。他们称自己的教室是“幸福教室”。
此时,“综合改革”的方法论背后,应对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当我们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前来加以研究时,“人”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过去,我们教育出了太多的具有碎片化知识的学生,在成为杰出人才的道路上,这是一种“天然缺陷”。今天的改革,我们不能不重视它,反省它,也许,当综合改革的方法论深入每个人心里时,教育会达成预想不到的超越
完备的制度必然改变教育的面貌吗?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稳定的制度。
可是,一套完备的制度就必然能彻底改变教育的面貌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曾参与特长生加分考试的评审工作。
考生里,一个来自山西的孩子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有教授问了他一个有关强拆的案例,让他谈谈看法。结果男孩讲到:之所以闹这么大,就说明政府还不够强硬,太软弱。
当时,王人博忍不住开导他:“孩子啊,你不能这样看,咱们都是普通人,但政府是个强者……”没等他说完,男孩子抢话道:“老师,能允许我用另一套话来说吗?”
“我觉得特别悲哀,年轻人完全没有原则,老师认同哪一套就讲哪一套,只要能加上那20分。“大致算来,让王人博感到“悲哀”的这位学生,应该是比较完整地接受了十年课改的那一批学生。
为什么在这些学生身上,我们看不到教育改革梦寐以求的独立个性、自由思想?过去十年,有关课改的各项制度(如选修课制、学分制、综合评价制)不断建立,我们以为,通过制度带动教学方式、学校文化、师生关系等方面的改变,就能培养出一代新型人才。
十年里,小组合作、多元评价渐渐蔚然成风,选修课让学生有了选择的权利,知识的传递更加高效,学生的表达、合作能力更加提升。但是,为什么离理想的教育还是有差距?
关键是教育的精神内核,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
教育的精神内核从何而来?从局长、校长、教师的教育理念而来。
也许有人会说,自主合作探究不是教育理念吗?但我以为,它们更多是一种教育教学的原则或程序。就逻辑关系而言,教育教学技术(如导学案、小组学习)是根据原则设计的,原则是根据原理或理念提出的。事实上,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背后,有更上位的教育理念,而理念的核心,则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马克思·韦伯语)
在我看来,我们的教育正是缺少了“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追求。其中两点最重要,一是挑战权威;二是宽容。
即便到了现代,中国仍然承载着“等级社会”所赋予的丰富性和沉重性,到处浸透着对权威的尊重和服从。校长、教师所作的一切,不是为了教育的长远,而是为了让“领导放心”;学生所作的一切,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自身的发展,而是为了得到校长和教师的认可、获得更好的分数和成绩。在这种风气之下,给学生再多的选择自由、再多的学习自主,最终得到的也只能是“划一”和“整齐”。
在国际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成绩并不靠前,但当代许多大的创新都出自美国。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教育中深藏着“挑战权威”的基因。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有一位印度朋友在美国执教。一次,这位印度人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的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教育甚至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与他们相比,我们对权威的尊重,尽管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质疑。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从众和融入群体而得到了奖励,他怎么会再去与众不同地冒险、探索新天地?我们培养了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教育理想,又怎么可能实现?
和挑战权威相伴的,是宽容。
学者胡适曾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说自由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种制度。当我们说宽容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价值追求。制度不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理念上,那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应该说,目前改革所构建的一系列制度,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能够自由发展,但缺少宽容的基础,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浅自由”,或者说是“伪自由”: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是不自由的;过程看似是自由的,但结果是不自由的。
2013年,上海市中考的作文题目是《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考试当天,有记者在考场外采访,一位学生说:“如果真话心里话,一定考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一旦真说心里话,就很可能是与评卷标准不符的“异质思维”,而对“异质思维”,我们向来缺乏宽容。
记得几年前,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英国皇家学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曾谈到,到目前为止,印度至少在一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这就是教师和学生在选择研究课题、表达和检验一些比较异端想法的自由度上更大。他强调,这种自由度是创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自由度及其背后的宽容,又何尝不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衡量标尺呢?只有在宽容的文化氛围里,我们才可能形成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师生可以大胆挑战权威、可以从容表达自己的思考,各种观点、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从而让整个教育呈现出一种泼辣辣的生机。
我们希望,从事教育的人和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以不完美,但一定不要唯唯诺诺,而是有棱有角,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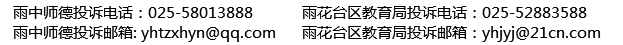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 32011402010587号
苏公网安备 3201140201058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