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歇,逐梦去
- 发布时间:2024-04-24 09:40
- 作者:汪惠
- 审核人:李发志
- 浏览量:630
“暴风”歇,逐梦去
汪惠
进入高三学期了,年级主任通知我,班上要转来一名新学生。稍微打听了一下,是上一届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休学一年,现回归学校想正常参加高考。第一眼看到他:身材高大,弯着背,精神不济,眼睛像没睡醒睁不开的样子,两边面颊也许因为还处于青春期的缘故有着明显的痤疮痕迹,头发稀疏,中间隐隐能看到肉色的头皮。没有多说什么,他安静地坐到了班级后排的座位上。
最开始一个星期相安无事,能正常和老师沟通,上课也抬着头听讲,十分本分。我还想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经历过一年的休息调整,应该恢复了吧,能顺顺利利在班学习参加高考,甚好。后来发现,自己高兴的太早了。先是自习课上逮到了他在桌子底下玩手机,然后班上老师反馈课上讲到一些题目当他存在分歧观点时,他会不自觉跳出来特别激动地大声驳斥老师,抒发自己的意见,影响课堂整体授课秩序和进度,其他同学意见很大。同时,和班上同学有时候相处遇到矛盾处也会突然爆发,出现骂人等激进行为,同学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暴风哥”,一点就炸。更严重的是,随着高三学习时间的拉长和学习强度的加大,他对于从早到晚甚至节假日都要上课的一些安排愈加反感,意志消沉,开始请假,从半天到一天再到一连好几天不来学校,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
盯着手机上他姑姑又一次发来的请假短信,隔着绿莹莹的屏幕和文字我也能清楚地读出背后的无可奈何:“老师,他今天又不肯去上学,他爸妈也不在,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我也发现,自从他来班后,进入班级家长群,平时请假等和我直接沟通的事宜出面的都是他姑姑,他的父母似乎从未露面。考虑到他目前的困境和之前因为心理原因休学的前情缘故,我决定做一些工作,其实内心里也清楚我的工作不可能在根本上帮他解决心理问题,甚至可能是病理上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观察他身上的难能可贵的一些品质:真诚、善良、正直,我也想通过我的一些努力让他回归校园的生活稍微轻松缓解一点。
首先,借着周末家长会时间,我提前和他的姑姑约了单独谈话的时间。了解到,他的父母都在上海做生意,比较忙,主要是姑姑在管他。家里兄弟两人,哥哥已经结婚,平时是住在哥哥家,和家里人沟通比较少,更多得是在家摆弄电子设备打游戏。
考虑到他之前心理原因休学,我联系了学校心理老师,调取了他之前的心理调查表。绝大多数时候他的情绪是低落沮丧的,谈到受到过的心理创伤时他写到,小学时候和父母在一起,被安排在上海的学校借读,班上的同学因为他是外地人都排挤孤立他。
同时,和班上同学、老师关于他进行了了解,进班后他和班上一些男生因为游戏等共同爱好逐渐熟悉,平时关系友好。同学、老师眼中的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直性子且容易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孩子,高兴的时候学习投入,不高兴时候会往桌椅上一趴蔫一整天。文科课堂上,特别是语文和政治老师谈到某个话题时,他会就某个字眼纠结到底,某个观点争辩到底,切话里话外想传达的观点是:世界是不公平的、黑暗的,努力是无用功。
最后,我决定和他本人聊一聊,了解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他在交流过程中袒露到,虽然家里的经济支持很充足,要求基本上都能被满足,但父母不在身边还是让他感到孤独,很多时候压力找不到人倾诉,排解没有渠道,在网络世界里转移注意力。网络信息爆炸,他很早时候比同龄人接触到更多的社会新闻,因为小时候在上海被排挤的经历,他逐渐觉得财富地位决定了在社会上话语权,高中阶段这么辛苦是不值得的,毕竟出来也是要打工,改变不了什么。高一入校后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因为心理原因经常请假,成绩下降,内心的落差感很大。目前和班上同学、老师相处整体比较愉快,但是有的时候一句无心的话可能会戳中他敏感的内心,让他当下暴躁失控或者抑郁难受,需要时间来缓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对他的状态愈加关注,也会时不时的和他以聊天的形式进行轻松的交流。愈是观察,我愈是能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缺人时,他会主动承担起倒垃圾、打扫卫生的脏活累活;考试搬考场时他会将不在同学的书本安排妥当不丢失;高考体检时前面的男孩子害怕抽血,他会在后面用手捂住同学眼睛,低声安慰;高三运动会班级拔河比赛他冲在第一,出力最大。平时情绪失控时和老师、同学有矛盾,缓和一段时间后,他会意识到自己欠妥的一些行为,事后主动道歉。课堂上,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且善于思考,经常和老师互动热烈,带动班级学习氛围。
私底下,我联系上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一个朴实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忙于生计,不能陪孩子有愧疚,希望他好好读书上大学,但对于现状无能为力。我安慰了这名母亲,把自己观察到的点滴细节和他身上诸多优点一一说给她听,告诉她这个孩子渴望亲情,渴望陪伴,在这个阶段适当引导,未来可期。
在高三多次考后教师会上,谈到他,我都会和班上老师叮嘱:这个孩子本性不坏,有时候太过执拗,老师们一视同仁地同时多给他点耐心和宽容。如果课堂上遇到他激烈争辩的题目,希望老师们先安抚他的情绪,照顾整体节奏正常讲解,不指摘不多说,但欢迎他课下来交流,他也逐渐接受了这种相处模式。
我的课上讲解阅读理解时,试卷上偶尔也会遇到他纠结驳斥的观点,先肯定他思维灵活,观察细致,深入思考;更多的时候课下深入讨论。课上谈到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时,他总能插上嘴产生联想引申,我也很乐意适度和他探讨并回应,活跃课堂气氛。作为班主任,也引导班上的同学多理解宽容他的一些冲动行为,好好相处。
再后来,他妈妈从上海回来了,决定最后冲刺阶段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陪伴孩子,打理他的一日三餐。非常明显,渐渐地,他能够比较长时间地坚持在班学习,学习状态好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甚至在高三下的一次大型考试中取得了从班级二十五名跃居到第九名的好名次。我把这些好的转变都和他妈妈分享,内心十分欣喜看到这样的转变。
当然,故事也并有到此结束,在高三漫长煎熬的后半期,他的心理问题还是出现了反复,又不愿意来学校了。在他不在班的日子里,我一直和他妈妈保持联系,了解他的动态。班上的重要活动都通知到位,希望他能参加,也转达班上同学对他的想念,希望他早日回归集体。好不容易他在班的场合里,也要找机会和他交流,尽量不说教,只是谈谈过去在班他的一些小细节再鼓励鼓励他坚持;谈谈对未来的想法,告诉他读大学并不是一定能保证什么,但是会给自己更多选择的机会,不妨尝试体验一下;也谈到了他妈妈,那个请假带他外出旅游缓解心情,有段时间腿伤了还一瘸一拐雷打不动中午来学校送饭的普通母亲。印象最深的是高三百日誓师的场合上,他在那场“你想对班主任/学生说些什么?”环节主动登台,我也略带忐忑地当着全年级的同学面前肯定了他的真诚善良,表达了自己对他最真挚的期望和祝福。
终于,高考落下了帷幕,他顺利参加并完成了高考。6月24那晚,他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他考了522分,“我都没想到他能正常参加高考,这个分数也是没想到,谢谢老师您对他一直以来的包容和鼓励!”尽管还是略有遗憾他在考前一周还是因为没能来校,数学成绩拖了后腿,但我想这可能已经比最开始预想的结局已经好很多了,也就释然了。
虽然仅仅只相处了短暂的一年时间,这股“暴风”却给我的教学生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我学会了怎么和这样的特殊学生相处,我想无外乎是给予尊重,肯定和鼓励,尽心尽力地教育付出,顺其自然地看着他们不断成长,离开高中,接着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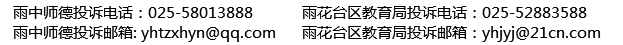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 32011402010587号
苏公网安备 32011402010587号
